我叫潘志诚今年82岁,是一名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老兵,1951年5月参军。1952年10月,17岁的我“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当时我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公安四十三团三营十连任文化助教。1953年9月回国,战争考验了我,19岁那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朝作战
1952年10月里的一天,我当时正在给十几位战士上文化课,忽然接到停止上课的命令,马上到团部(浦东新场镇)整训,并作长途行军的准备。当时十七岁的我作为一个小战士,还不能理解这个命令的意义,但是老兵们都意识到:“部队要去打仗了!”
1951年16岁的潘志诚
我虽然只有十七岁,但是因为读过中学又拥有一年半军龄,所以被提拔为军队文化助教。虽说我是一名战士,但是部队并没有给我配发枪支弹药,全身的装备只有被褥、布鞋和一些文具,年轻得我随着连队轻松步行了三十多里路抵达团部。在团部我们进行了三天的动员学习,通过表决心和写申请报告等活动,充分显示了我军政治思想工作的力量——有些战士咬破手指写血书,我也用针在无名指上扎了两针,在决心书上盖了手印。这些行为都来自于一个革命战士发自内心的坚强决心与信念。我们团有两千多人,每人都有一本来自旧社会的血泪史,大家都遭受过战争和旧社会的苦,馨竹难书的往事让战士们个个摩拳擦掌,积极要求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保家卫国。
离开新场镇的那天,我除了手榴弹外,步枪、子弹和米袋都有了,此外我还多了五样东西:一块小黑板、一把胡琴、一根笛子、一个篮球和一副竹板。部队行军走得很快,我咬牙紧跟,不要一天时间我们就从新场镇走到了江湾火车站。我们在江湾火车站坐上了开往丹东(当时称为安东)的列车,火车开了四天四夜抵达丹东。一下车我就感受到了战争的气氛,当时丹东火车站已经被敌军飞机炸毁,鸭绿江大桥上到处是弹孔,街上行人稀少,一片战争景象展现在我们眼前。在丹东修整两天后,我们进行了“再动员”,军官向我们交代了入朝事宜。
战火中的丹东
我们正式入朝前,为了迷惑敌人而换乘货运列车,这是为了不让敌军发现我们是一辆运兵列车而减少轰炸概率。上百人缩在狭小的车厢内,默默进发,车厢里鸦雀无声为的是不暴露行踪,当我们抵达平壤时正是凌晨二时。
1951年,潘志诚刚入伍时,全班合影
战争中的平壤,真是惨不忍睹:残垣断壁上布满弹痕,零下三十度的天气伴随着鹅毛大雪,大雪覆盖着整片整片的战争废墟,场景甚是凄凉。长途跋涉加上饥饿难耐,我们下车后就开始在防空洞里烧饭。我实在是饿极了,一口气就喝了十几军碗的稀饭。经过简单修整之后,我们开始了昼夜行军,行军时八斤重的羊皮大衣必须反穿,因为反穿可以与雪同色便于隐蔽。
我的主要任务就是协助连长鼓舞战士们的士气,确保部队安全抵达驻防地点。我站在高地上,用“上海普通话”打起竹板唱起快板书,弄得大家捧腹大笑,战士们的情绪一下子高涨起来,整个行军过程中无一人掉队。在行军中,我们不时遇到敌机扫射,我们就趴在雪地中隐蔽,确认安全后再行军。就这样经过连续七个晚上的急行军后,我们到达了驻防地点——马洞市。
重磅炸弹
我第一次看到美国飞机投弹,是部队安顿好后的第二天。那天晴空万里,一清早我们部队正好执行搬运粮食的任务。由于任务不重加上天气晴朗,大家的情绪都不错。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东南方向开始响起轰隆隆的引擎声,老兵一听声音便知情况不对,这飞机过来应该不是轰炸就是机枪扫射,便提醒大伙赶紧做好防空准备。我初来这片陌生的战场,难免好奇美国飞机是什么样的,于是便张大眼睛望去:三架飞机呈三角队形在我们阵地上空盘旋一圈后就开始俯冲,每架飞机投放两颗炸弹。我清清楚楚看见每颗炸弹尾部有几圈红白相间的油漆涂装,涂装下面是三个扇装的弹翼……这时,副连长看到我还在抬头观望就急着高喊:“小文教,趴下来!快!”这时我如梦初醒,纵深向身旁的弹坑纵身一跃,与此同时六枚炸弹在我不远处同时爆炸,我吓得不轻。从此,我懂得了飞机轰炸是怎么一回事。
敌军轰炸
随着战争的进行,每天与飞机轰炸打交道的我们懂得了飞机炸弹有多少种类:有落地即爆的各类炸弹,最重的有五千斤,最轻的有六十斤;有横在公路和铁路上的定时炸弹,这种定时炸弹有几分钟甚至几小时的定时;有那种钻在泥土里几天、几周甚至几年的定时炸弹;此外敌机还会投放照明弹、燃烧弹,还会有杀伤力很大的子母弹、蝴蝶弹和三角钉炸弹等等。
1952年在朝鲜四十三团团部
我们摸索到不同的炸弹有不同的性能,学会了如何应对这些炸弹。重磅炸弹虽然破坏力很大,但是对于士兵的杀伤力有限,只要不是直接命中,基本不会对士兵有太大杀伤。有一个晚上,美国一架重型轰炸机在我军驻地上投下一枚五千斤的炸弹。投弹造成的弹坑像游泳池那么大,积水有一米多深,翻起的泥土把我们的防空洞压得严严实实,我们都被“活埋”在防空洞里。临近部队立即前来营救,他们一边铲土一边议论:“这个部队完了,就是有活的也剩不下来几个了。”挖了一个多小时,我们三个防空洞的人员竟然都无一伤亡地走了出来。
子母弹
但是,那些子母弹弹体虽小,可弹片一旦击中士兵往往非死即伤。一个严寒的晚上,几架轰炸机在我们排的一个哨所周围投了几枚子母弹,正在执勤的一班长被弹片击中,整个右肩膀都被打了下来,断臂与躯干间只连着一层皮。当时,一班长还感知不到自己已经受伤,只知道自己不能抬枪了。由于医疗条件有限,一班长的手臂接了上去,但是仍然截肢了一大截,而且手臂接装反了。我们团在整个朝鲜战争中伤亡并不多,但是仍有二十多名战士永远留在了朝鲜土地上。
“炸不断 打不烂”的钢铁运输线我们入朝作战的主要任务是防空哨,所谓防空哨就是保证在敌机空中封锁下,将后方的人员与物资源源不断运往前线,打造一条从鸭绿江到三八线“炸不断 打不烂”的钢铁运输线。
我军的物资运输线
朝鲜战场上,我方所有的公路、铁路、桥梁、隧道以及各种建筑都是美国飞机的攻击目标。因为当时的通信手段非常落后,当我方运送物资的车辆遭到敌机空袭时,后续的运输车辆毫不知晓仍在继续行进。特别是到了晚上,美军发射照明弹往空中一挂,我军行进中的车辆无法隐蔽,任凭敌机狂轰滥炸,我军物资车辆损失惨重。为了改变这一不利局面,我军设计了很多通报敌情的方法:一开始我们是利用敌机扔下来的未爆炸的重磅炸弹,卸下引信和炸药,把弹壳挂在预制架上,像寺庙中的洪钟一般敲击弹壳。敲击弹壳的声音便于识别,500米一个岗哨,每个岗哨配备一个“用弹壳做成的钟”进行敌情传递。这个方法虽然有效,但是由于钟声传递的速度慢、音量差和距离近,后来我军开始采用步枪枪声传递敌情。步枪传递的优势在于“速度快、声音响、传递快”,从三八线传递到鸭绿江十分钟之内即可传递情报完毕,有效保障了交通线的防空。
志愿军运输线
由于上述原因,一个连队驻地往往分散得很开,战线拉得很长,部队每天与敌机捉迷藏。我们每天鸣枪传声,弄得敌空军奈何不了我们。于是敌军恼羞成怒,开始24小时狂轰滥炸,向任何有可能的目标进行无差别轰炸。战士们在炮火中成长:我们凭借声音就可以辨别飞机的类型,预料敌机的任务,投放的是什么类型炸弹以及飞行方向。
1954年华东公安十五师师部
就是在这样的战争环境中,防空哨里发生了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有一位营长勇救朝鲜人民军副总参谋长李相朝,荣立一等功,荣获三级国际勋章;防空哨战士们在公路上排除大量定时炸弹、蝴蝶弹以及各种杀伤弹,荣立战功与奖章。我因在一年的战斗生涯中,不怕牺牲,荣立三等功,荣获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颁发的军功章一枚。
美国飞机的扫射
1953年2月的一天,那天阳光灿烂,虽然春寒料峭但是能感受到一丝丝暖意。我走进驻地附近苹果园,发现有许多又大又新鲜的野菜,于是开始一棵一棵挖野菜。约上午九时左右,东南方向飞来二架美国战斗机,我想自己不过是一个人在挖野菜,敌机应该不会将自己作为目标。出乎意料的事情来了,两架飞机朝着我扑过来开始扫射。我无处躲藏,只能就近寻找掩护,敌机对着我来回扫射了五轮罢休而去,我才逃过一劫。
1953年,潘志诚十九岁
战地鼓动
连队120多人,因为我在连队年纪最小,又是文化助教,每人都叫我“小文教”。我的主要任务就是在战地鼓动对敌作战工作。唱歌是连队文化的重要方面,老兵们大多数没有文化不懂音符,把所有音节都唱成一个调。即使如此,他们唱歌欲望还是非常强烈。我们唱的都是铿锵有力的革命歌曲,如《解放军进行曲》、《我是一个兵》、《大刀进行曲》等,还有很多家乡小调。每逢开会,每个排或班都有几个活跃分子,相互拉唱。我虽不擅长唱歌,但是不怕难为情,即使走调了还是教着大家唱歌。为了提高各连队文教唱歌水平,团政治部办了一个星期的文教训练班,培训我们这些文教唱歌。
1956年,潘志诚二十一岁
朝鲜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战士们都觉得朝鲜歌好听,希望“小文教”能教他们唱朝鲜歌。我答应了他们要求,我于是一边学朝鲜语,一边学歌,我先后向朝鲜阿玛尼(老大娘),阿爸基(老大爷)及阿德尔(小孩子)学会了《金日成将军之歌》、《保卫祖国》、《人民军进行曲》、《桔梗歌》等朝鲜歌,同时还学会了些朝鲜基本舞步,便开始认真地教战士们唱朝鲜歌,跳朝鲜舞,大家兴致很高。
1962年,潘志诚二十七岁
我编写的黑板报是连队三位文教中编的最好的一位,每周出版一期或二期,粉笔只有白、红、绿三种颜色,但也颇受战士们好评。当时,有一位江苏籍的小战士比较任性,动不动与人吵架,但是他挖“单人掩体”挖得又快又好,我抓住他的这一特点写成快板登在黑板报上,连登三期,触动了他,他不好意思地对我说:“小文教,你不要写了,我保证不吵架了。”为此,新民主义青年团四十三团团委通报表扬了我。
立功受奖1953年7月,交战双方于朝鲜板门店签订《朝鲜停战协定》。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军民无比欢欣鼓舞。在胜利的喜悦中,我们连于1953年9月16日在马洞市的一个废墟上召开了庆功大会和颁发抗美援朝纪念奖章典礼,我被评为三等功,荣获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颁发的军功章一枚。立功喜报传至老家上海南汇,乡亲们在村干部带领下,敲锣打鼓向我父母报喜,乐坏了双亲。
《朝鲜停战协定》签订
庆祝大会结束后,连队与驻地朝鲜老百姓进行了告别大联欢,我用朝鲜语唱了一首《金日成将军之歌》,指战员们与朝鲜群众一同载歌载舞,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中。当联欢会结束时,一位朝鲜大妈将一把铜调羹送给我,含着泪水对我说:“孩子啊,你回到中国后别忘了大妈啊!”我向她深深鞠了一躬,收下了这把铜调羹,说了一句朝鲜语:“抗桑米大(谢谢)!”
凯旋归建
1953年9月下旬,我团奉命回国归建。回国,对一个战胜强大敌人的部队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胜利的喜悦!见到同胞和亲人的喜悦!从丹东出发到朝鲜,“祖国”两字对于从异乡战场而归的战士是多么的亲切和温暖。我们从马洞市踏上火车,经过7个多小时的行程,到达朝鲜北部与祖国吉林隔江相望的江界市,下车后沿着鸭绿江步行五天至吉林省临江市与朝鲜接壤的大桥处,部队停止行进,部队就在这里驻扎下来。团首长向全团指战员进行了回国前的动员:“虽然我们要归国了,但是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随时会向我军打冷枪。
志愿军凯旋
鸭绿江的桥梁上和渡口,布满了美其名曰维护停战的联合国军。”由16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军,随时准备刺探我军情,我们之所以选择临江大桥回国,因为这里是唯一不设联合国军队的大桥。虽然战争结束了,但是撤军仍需要秘密进行,不能让志愿军撤军的消息泄露。
1975年在五七干校
通过大桥的当晚,每一个人都作了严格检查,背包及携带的装备都保证不能发出声响。我们几乎是小跑步地通过了大桥,上火车时已经是第二天凌晨一时。火车途径通化市时已经是早上八点钟,这时我透过窗望去,车站到处是横幅标语,原来今天是国庆节!是建国四周年的纪念日!我们高声欢呼:祖国万岁!毛主席万岁!那种高兴与自豪是难以言表的。经过三昼夜的火车行程,我回到了上海,归建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公安部队第15师建制,继续自己的军旅生涯。






















 1
1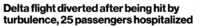 2
2 3
3 4
4 5
5 6
6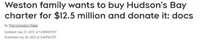 7
7 8
8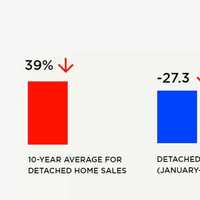 9
9 10
10 1
1 2
2 3
3 4
4 5
5 6
6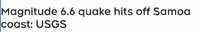 7
7 8
8 9
9 10
10






